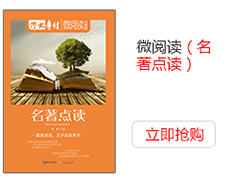大师福克纳:从这里开始
作者:
范司永
分类:
精品阅读
子类:
读点经典
福克纳的《熊》是美国文学界公认的一部佳作,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认为《熊》在福克纳小说中的地位可以和《比利·巴德》在梅尔维尔作品中的地位以及《老人与海》在海明威作品中的地位媲美。
福克纳以浪漫主义的诗性想象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记录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与真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永恒深远的美国童话。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熊》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人、社会、自然如何能够和谐地三位一体?倘若继续对自然无节制地、贪婪地索取,那无疑是自取灭亡。
《熊》的情节较为简单,整个故事共分五章,主要描写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方边疆地区正在被蚕食。前三章整体描叙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从10岁起,年年随狩猎队到镇北荒野去打猎。他们的对手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老熊—“老班”。他们须用崇高的原则、公正的行为与之周旋。在其过程中,艾萨克逐步掌握了打猎的技能,并培养出只有在打猎中才会具有的男性美德:怜悯、勇敢、谦逊、仁爱和牺牲精神。艾萨克16岁那年,老班终被布恩·霍根贝克和一条名叫“狮子”的杂种狗杀死。
在第五章里,艾萨克再次回到狩猎的荒野,时距老班之死已过两年。一切皆非往日面貌:德斯班少校已把荒野卖给了一家木材公司,象征现代的“文明”——铁路、伐木工人为获利而毁坏了荒野——已经玷污了这片未开垦的圣地,“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地被人们用犁头和斧子残食”。大熊、山姆·法泽斯之死暗示了荒野危在旦夕。最后一个会说“古老的土语”的人—山姆,几乎与大熊被杀死的同时,从驴背上摔下,再也未能站起。山姆死后,按照他的遗愿,艾萨克和布恩一起用古老的仪式将他埋葬。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可以算是他的文学宣言,他正是通过《熊》等作品来表达他的这些思想的。福克纳说:“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作家颂扬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独存”。他又说,“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是人合作价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事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当我们重新解读福克纳的《熊》时,发现小说的最终目的关注的不仅是艾萨克个人的命运,而且是美国、整体人类的未来。艾萨克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他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道德标准却覆盖了全世界,覆盖了全人类。福克纳不仅歌颂了人类普遍赞扬的一些美德,还提出了值得人类深思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要征服大自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大自然,怎样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地三位一体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课题。福克纳正是通过大熊老班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摘自《语文教学与研究》
《熊》:一个永恒深远的美国童话
他后来才明白,整个事情早在这次打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在那一天之前就己开始,当时他还没有第一次用两个数字写自己的年龄,他的表外甥麦卡斯林也还没有第一次带他到打猎帐篷里来,到大森林里来,让他向荒野为自己争取猎人的称号与资格一一这就要看他方面有没有足够的谦逊与毅力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见到过那只巨大的老熊,但他已经继承了熊的精神,那只被捕兽夹伤过一只脚,方圆百里之内无人不知,象个活人似的享有盛名的熊。关于大熊的传说多得很,说它如何经常拆坏谷仓,把储藏的玉米棒子偷走,说它如何把一整只一整只的猪娃、大猪,甚至牛犊拖到森林里去吞吃掉,如何捣毁陷阱,打翻捕兽夹,把猎狗撕咬得血肉模糊,死于非命,又说猎枪近距离照直了对它放,霰弹落在它身上如同小孩从竹筒里吹出来的豌豆,一点也不起作用——总之,简直就是一部小艾克出生前即已开始的破坏与毁灭的历史。在这部历史里,毛茸茸,硕大无比的大熊像火车头,速度虽然不算快,却是无情地、不可抗拒地、不慌不忙地径自往前推进。在孩子见到大熊之前,脑海里已经常常出现它的形象。大熊在他的梦里蒙蒙胧昽地出现,高高地耸立着。当时,孩子甚至都没有见到过这片未经斧钺的森林。在森林里,大熊留下了它那歪扭的脚印,这头毛糁後、硕大无朋、眼睛血红的大熊,它并不邪恶,仅仅是过于庞大。对于想用一通吠叫把它吓住的猎犬来说,它是太大了,对于想用奔驰把它拖垮的马儿来说,它是太大了,对于人类和他们朝它打来的子弹来说,他是太大了,甚至于对它赖以生存、日益局促的荒野与森林来说,他也是太大了。孩子似乎已经用直感察觉出他的感官与理性没有告诉他的东西:荒野是注定要灭亡的,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不断被人蚕食,用犁头、用斧子。人们害怕荒野,因为它是荒野。人们多的不可胜数,彼此间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是那只大熊却享有盛名。孩子也知道在荒野里飞跑奔突的甚至都不是一只会死的野兽,而是一个从已逝的古老年代里残留下来的顽强不屈,无法消灭的时代错误,是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化了的痕迹。孱弱瘦小的人类对古老的蛮荒生活又怕又恨,他们愤怒地围上去对着森林又砍又刨,活像对着打瞌睡的大象的脚踝刺刺戳戳的小矮人,——这只老熊,孤独,顽强,形单影只;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无所谓死亡——简直就是丧妻失子的老普里阿摩斯。
摘自《熊》,上海译文出版社
读经典:
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福克纳是一座美国现代文学上的险峰,他的作品虽然风光无限,气象万千,却不允许我们匆匆地闯入。在小说《熊》中,福克纳运用新颖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隐喻表达,不仅为提供了新奇独特的审美体验,而且生动地展现了现代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表现了福克纳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熊》文章象征、意识流气息浓重,是美国文学界公认的一部佳作,被誉为“解读福克纳全部小说乃至美国南方文学的钥匙”。 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认为《熊》在福克纳小说中的地位可以和《水手比利·巴德》在梅尔维尔作品中的地位以及《老人与海》在海明威作品中的地位媲美。
福克纳以浪漫主义的诗性想象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记录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与真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永恒深远的美国童话。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熊》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人、社会、自然如何能够和谐地三位一体?倘若继续对自然无节制地、贪婪地索取,那无疑是自取灭亡。
《熊》的情节较为简单,整个故事共分五章,主要描写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方边疆地区正在被蚕食。前三章整体描叙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从10岁起,年年随狩猎队到镇北荒野去打猎。他们的对手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老熊—“老班”。他们须用崇高的原则、公正的行为与之周旋。在其过程中,艾萨克逐步掌握了打猎的技能,并培养出只有在打猎中才会具有的男性美德:怜悯、勇敢、谦逊、仁爱和牺牲精神。艾萨克16岁那年,老班终被布恩·霍根贝克和一条名叫“狮子”的杂种狗杀死。
在第五章里,艾萨克再次回到狩猎的荒野,时距老班之死已过两年。一切皆非往日面貌:德斯班少校已把荒野卖给了一家木材公司,象征现代的“文明”——铁路、伐木工人为获利而毁坏了荒野——已经玷污了这片未开垦的圣地,“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地被人们用犁头和斧子残食”。大熊、山姆·法泽斯之死暗示了荒野危在旦夕。最后一个会说“古老的土语”的人—山姆,几乎与大熊被杀死的同时,从驴背上摔下,再也未能站起。山姆死后,按照他的遗愿,艾萨克和布恩一起用古老的仪式将他埋葬。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可以算是他的文学宣言,他正是通过《熊》等作品来表达他的这些思想的。福克纳说:“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作家颂扬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独存”。他又说,“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是人合作价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事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当我们重新解读福克纳的《熊》时,发现小说的最终目的关注的不仅是艾萨克个人的命运,而且是美国、整体人类的未来。艾萨克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他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道德标准却覆盖了全世界,覆盖了全人类。福克纳不仅歌颂了人类普遍赞扬的一些美德,还提出了值得人类深思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要征服大自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大自然,怎样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地三位一体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课题。福克纳正是通过大熊老班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摘自《语文教学与研究》
《熊》:一个永恒深远的美国童话
他后来才明白,整个事情早在这次打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在那一天之前就己开始,当时他还没有第一次用两个数字写自己的年龄,他的表外甥麦卡斯林也还没有第一次带他到打猎帐篷里来,到大森林里来,让他向荒野为自己争取猎人的称号与资格一一这就要看他方面有没有足够的谦逊与毅力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见到过那只巨大的老熊,但他已经继承了熊的精神,那只被捕兽夹伤过一只脚,方圆百里之内无人不知,象个活人似的享有盛名的熊。关于大熊的传说多得很,说它如何经常拆坏谷仓,把储藏的玉米棒子偷走,说它如何把一整只一整只的猪娃、大猪,甚至牛犊拖到森林里去吞吃掉,如何捣毁陷阱,打翻捕兽夹,把猎狗撕咬得血肉模糊,死于非命,又说猎枪近距离照直了对它放,霰弹落在它身上如同小孩从竹筒里吹出来的豌豆,一点也不起作用——总之,简直就是一部小艾克出生前即已开始的破坏与毁灭的历史。在这部历史里,毛茸茸,硕大无比的大熊像火车头,速度虽然不算快,却是无情地、不可抗拒地、不慌不忙地径自往前推进。在孩子见到大熊之前,脑海里已经常常出现它的形象。大熊在他的梦里蒙蒙胧昽地出现,高高地耸立着。当时,孩子甚至都没有见到过这片未经斧钺的森林。在森林里,大熊留下了它那歪扭的脚印,这头毛糁後、硕大无朋、眼睛血红的大熊,它并不邪恶,仅仅是过于庞大。对于想用一通吠叫把它吓住的猎犬来说,它是太大了,对于想用奔驰把它拖垮的马儿来说,它是太大了,对于人类和他们朝它打来的子弹来说,他是太大了,甚至于对它赖以生存、日益局促的荒野与森林来说,他也是太大了。孩子似乎已经用直感察觉出他的感官与理性没有告诉他的东西:荒野是注定要灭亡的,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不断被人蚕食,用犁头、用斧子。人们害怕荒野,因为它是荒野。人们多的不可胜数,彼此间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是那只大熊却享有盛名。孩子也知道在荒野里飞跑奔突的甚至都不是一只会死的野兽,而是一个从已逝的古老年代里残留下来的顽强不屈,无法消灭的时代错误,是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化了的痕迹。孱弱瘦小的人类对古老的蛮荒生活又怕又恨,他们愤怒地围上去对着森林又砍又刨,活像对着打瞌睡的大象的脚踝刺刺戳戳的小矮人,——这只老熊,孤独,顽强,形单影只;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无所谓死亡——简直就是丧妻失子的老普里阿摩斯。
摘自《熊》,上海译文出版社
读经典:
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福克纳是一座美国现代文学上的险峰,他的作品虽然风光无限,气象万千,却不允许我们匆匆地闯入。在小说《熊》中,福克纳运用新颖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隐喻表达,不仅为提供了新奇独特的审美体验,而且生动地展现了现代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表现了福克纳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熊》文章象征、意识流气息浓重,是美国文学界公认的一部佳作,被誉为“解读福克纳全部小说乃至美国南方文学的钥匙”。 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认为《熊》在福克纳小说中的地位可以和《水手比利·巴德》在梅尔维尔作品中的地位以及《老人与海》在海明威作品中的地位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