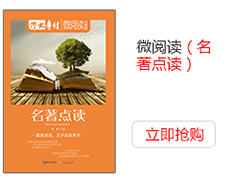热词:莫迪亚诺
作者:
匿名
分类:
作文素材
子类:
热词新语
事件: 2014年10月9日19时,,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其代表作有《暗店街》、《八月的星期天》等。莫迪亚诺获奖后,中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莫迪亚诺”热,主要作品销量节节攀升,人们也争相谈论其生平和小说。
声音
莫迪亚诺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也挺大。他跟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是齐名的,他们和另外一个法国作家合称为“法国当代作家三杰。”
——邱华栋
莫迪亚诺书写的是所有人的困境
——叶倾城
莫迪亚诺是行动的,更是盲动的普鲁斯特。
——评论家止庵
莫迪亚诺的作品“读起来不难”,“语言并不繁琐,但整个小说的构成十分精妙”。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隆德
《青春咖啡馆》是莫迪亚诺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作品中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调查与跟踪,回忆与求证,找不到答案的疑问。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贝尔纳·皮沃
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莫迪亚诺
素材链接
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黑马
寒一一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于10月9日星期四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根源大多来自他的童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有一段不平常的童年。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一生下来就由外公外婆照顾。两年后,弟弟鲁迪出世,兄弟俩被母亲扔给奶妈抚养。刚过十岁生日的弟弟突然病逝,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常讲到:“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后来他把自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题献给这个早夭的弟弟。
弟弟的去世,他是最伤心的一个人。他恨父母生他们而不养,那段时间,他和父母对抗。他变成一个坏孩子,来表达他的反抗。他经常从家里出逃,放任自流地在巴黎闲荡,去许多危险的、他那种年龄的孩子不该去的地方,有些街区一直让他感到恐惧,那种冲击非常强烈,也正是他的这段时间,成就了他的笔下之物。
他不好不坏地活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文学是他疗伤的方式。那些在青春期帮助他生存下去的诗人们: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阔比埃、查理·克罗、日耳曼·努沃、阿波利奈尔……他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父母。在他低迷之时,他们永远向他敞开心灵,给他倚靠。
后来父亲为了一个意大利女子与母亲分居了,为了接济穷困潦倒的母亲,莫迪亚诺开始到一些特别的人家或者图书馆偷书卖给一些书店的老板。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那里去要钱,父亲并没有帮他,反而向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这件事情,让他突然成长。他去了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便是在该社出版,让他崭露头角。
他找到了文学这根稻草,能够真切地救他。此后,他专事写作,著有二十余种小说,屡获大奖,直到2014年以黑马的姿态斩获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世人熟知。
(摘自《时尚北京》2014年第11期)
素材点拨
莫迪亚诺六十七岁,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是所有写作者至高的荣誉。他甚至感谢自己的童年,落难的少年时光,正是这些劫难造就了他的所有,尽管经历时有多么苦楚。可世界就是这样,得失永远在一线之间。
中国人应淡化诺贝尔文学奖
谭振江
2012年诺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华人世界对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梦想曾再次搅动了起来。但很多人却认为:中国人应淡化这一情结。
德国大哲人海德格尔曾告诫人们: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种语言方式,就是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民族传统,一种价值观念,甚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传承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汉字、汉语,浓缩了中国文化如生产方式、思维认知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内核形态,积淀了丰富的具有东方文化智慧特征的人文内涵,这哪怕是最发达的拼音文字也难以表述承载的。
中国一些优美的现当代小说,如果翻译成了拼音文字,想必也神韵大失。只要读沈从文、老舍、柳青、孙犁、贾平凹等作家所构筑的民族地域色彩浓厚,富有美妙传神东方绘画美特征的作品,相信就会认同了。
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字作品翻译成拼音文字,就必然降低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艺术档次,这又怎么能反映出汉语作家作品的真实水平呢?屈原、李白、苏轼的伟大诗歌作品一经翻译,如果凭译本,他们最多算是三四流的诗人。
相反,一些外国诗人作家的作品,经过中国诗人作家的出色翻译,往往就能凭借汉语言文字诗性美的凸现而提升档次。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普通诗作了。经鲁迅翻译加工,原本自由体作品变为语言工整而且有韵脚、琅琅上口的名篇了。还有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自白派”诗歌,就被诗人岛子和赵琼的翻译加工而声名鹊起。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及其华文、华语的复兴,指望西方只懂得拼音文字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无异是天方夜谭。如果有一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娴熟地阅读汉语言文字的文学作品,那就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勃兴之时。华文的诗人作家努力创造并期待着这一天,而不是期盼西方人设立的某个文学奖项。
(摘自《联合早报》)素材点拨
素材点拨
中国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信仰缺失,因为不知道追求的方向,所以一有相关奖项发布,马上趋之若鹜。诺贝尔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权威,我们应当看淡诺贝尔文学奖,以自信的眼光和态度来欣赏及本土文学优秀作品。
时文选读
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
姜伯静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让很多国人失望了,倒不是因为中国作家没有获奖,毕竟莫言已经得过一次,而是因为我们喜欢的村上春树又一次陪人家读书,又一次成了陪跑者。但仔细想一想,这个结果并不应该让人意外。因为在我看来,村上春树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莫迪亚诺属于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人。与流行元素相比,颁奖思维明显“滞后”于潮流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对于我们来说,莫迪亚诺是一位陌生的“熟人”。与很多“异军突起”的诺奖得主相比,莫迪亚诺在中国的文学市场绝不能算是一个“迟到者”,甚至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作为王小波、王朔曾经顶礼膜拜的“导师”,莫迪亚诺理应被更多国人知晓。只可惜,在王小波早逝、王朔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符号的今天,莫迪亚诺依然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属于另一代人一样。尽管在此之前,他在中国还未属于任何一代人。
但从文学写作本身来看,莫迪亚诺却真的属于另一代人。莫迪亚诺的文字,更多地注重过去、描写过去,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所言,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吴岳添编译的《塞纳河畔》中,有记者问莫迪亚诺当时(1993年5月)正读什么书、喜欢哪一类作家?他回答:“在二十世纪的作家当中,我年轻时印象最深的是从海明威到帕维泽,再近一点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不属于这一代人。”而他从《星形广场》开始的写作,恰恰印证着他的说法。
与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相比,村上春树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村上春树。尽管存在着种种误读,可我们很多人就是宁愿相信村上春树就是“挪威的森林”里的那棵树,就是小资,就是小清新。除去国别、民族的因素,因为喜欢,所以希望,希望村上春树能够得奖。只是很可惜,村上春树属于今天流行的时代,而他的拥趸似乎还没有掌握投票权,他的影响力还很难从民间影响到远在北欧瑞典文学院的那几位老同志,他的作品理念与“创作出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也相去甚远,他的人文理念噱头更是要比“德国占领时期”这几个字差得更多。所以,村上春树还需要再慢慢跑上几年。
其实,很多诺奖得主都是属于另一代人的,包括我们的莫言,因此这并不奇怪。据说,莫迪亚诺某部作品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仓库里还有很多本没有卖出去,借着这股诺奖的东风,不知会不会咸鱼翻身。而我们,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好好阅读一下这个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呢?
(摘自《北京青年报 》2014.10.12)
学生佳作
读书有三重
贾平凹老先生妙用了这样一句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再看水不是水;又看山还是山,又看水还是水……”
山水有三重,读书与品读经典不也如此?
品经典之一重: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格物是致知的前提,品读经典首先要回归到原著,唯有那流传千载,经时间的检验之后仍不露破绽的源头之作才是我们知识源源不断的活泉之水。
读《论语》,你要去吟哦那“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方能体悟大方之家的处世睿智;读《鸿门宴》,你需回归那字字如明玉的方形文字,读句读、品情节,方能获得那兵家之胜败之诀,处世之变通圆滑;读柳永的《雨霖铃》,你得去吟唱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方能感诗人之所感,从缠绵悱恻中体察世间真情。
倘若只从翻译后的书中读经典,文字带着冰冷的面具,何来精髓之悟?
品经典之二重:思之所至,赏玉鉴纹。
愚者如我,读书总是兴之所至,只识文字美不美。思之所至,赏玉鉴纹。真正的经典,字字珠玑,倘若只停留迷恋于文字之美,情节事物之光怪陆离,不免流于浅薄。
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否需要去思考轻与重之间的关系呢?你看看这活过的人生,想想那重虽是一种具体的可言说的负担,可那轻——虚无的轻,未必不比重更沉重百倍。虚无才是人生最难以承受的重量啊!
品经典之三重:自视所存,书已成镜。
王成玉曾言:“从来没有人在读书,而是在书中读自己。去发现自己,寻找自己。”当你在书中会晤先哲与智者,在电火石光中思想激撞的瞬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便是对经典的体察与感悟。
感悟常常流露于生活,生活的体验是对经典的再现。读赵明诚与李清照婚后琴瑟合鸣的时光:他们饭后坐归来堂烹茶,互问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胜者可先饮茶,“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他们把经典之爱延续到生活之爱,这才是经典的再创造再体验。
山水有三重,读书亦有三重。
先格物,再思考,而后看到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人生的绮丽。
午后,如果阳光澄清,往日已归去哪里?在生之极处,在思之极处。在温暖的午后,品读经典,岁月静好。
点评
作者从“格物——思考——看自己”三个层面展开,层层深入,阐述自己对阅读经典原著方法的独到见解。文章处处扣紧“如何阅读经典”这一话题,分析简洁、透彻而又有深度。行文中诗词佳句信手拈来,足见作者丰厚的知识积累,语言洗练,行文流畅,结构紧凑。作为考场作文,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实属难得。
声音
莫迪亚诺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也挺大。他跟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是齐名的,他们和另外一个法国作家合称为“法国当代作家三杰。”
——邱华栋
莫迪亚诺书写的是所有人的困境
——叶倾城
莫迪亚诺是行动的,更是盲动的普鲁斯特。
——评论家止庵
莫迪亚诺的作品“读起来不难”,“语言并不繁琐,但整个小说的构成十分精妙”。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隆德
《青春咖啡馆》是莫迪亚诺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作品中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调查与跟踪,回忆与求证,找不到答案的疑问。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贝尔纳·皮沃
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莫迪亚诺
素材链接
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黑马
寒一一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于10月9日星期四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根源大多来自他的童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有一段不平常的童年。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一生下来就由外公外婆照顾。两年后,弟弟鲁迪出世,兄弟俩被母亲扔给奶妈抚养。刚过十岁生日的弟弟突然病逝,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常讲到:“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后来他把自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题献给这个早夭的弟弟。
弟弟的去世,他是最伤心的一个人。他恨父母生他们而不养,那段时间,他和父母对抗。他变成一个坏孩子,来表达他的反抗。他经常从家里出逃,放任自流地在巴黎闲荡,去许多危险的、他那种年龄的孩子不该去的地方,有些街区一直让他感到恐惧,那种冲击非常强烈,也正是他的这段时间,成就了他的笔下之物。
他不好不坏地活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文学是他疗伤的方式。那些在青春期帮助他生存下去的诗人们: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阔比埃、查理·克罗、日耳曼·努沃、阿波利奈尔……他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父母。在他低迷之时,他们永远向他敞开心灵,给他倚靠。
后来父亲为了一个意大利女子与母亲分居了,为了接济穷困潦倒的母亲,莫迪亚诺开始到一些特别的人家或者图书馆偷书卖给一些书店的老板。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那里去要钱,父亲并没有帮他,反而向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这件事情,让他突然成长。他去了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便是在该社出版,让他崭露头角。
他找到了文学这根稻草,能够真切地救他。此后,他专事写作,著有二十余种小说,屡获大奖,直到2014年以黑马的姿态斩获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世人熟知。
(摘自《时尚北京》2014年第11期)
素材点拨
莫迪亚诺六十七岁,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是所有写作者至高的荣誉。他甚至感谢自己的童年,落难的少年时光,正是这些劫难造就了他的所有,尽管经历时有多么苦楚。可世界就是这样,得失永远在一线之间。
中国人应淡化诺贝尔文学奖
谭振江
2012年诺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华人世界对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梦想曾再次搅动了起来。但很多人却认为:中国人应淡化这一情结。
德国大哲人海德格尔曾告诫人们: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种语言方式,就是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民族传统,一种价值观念,甚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传承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汉字、汉语,浓缩了中国文化如生产方式、思维认知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内核形态,积淀了丰富的具有东方文化智慧特征的人文内涵,这哪怕是最发达的拼音文字也难以表述承载的。
中国一些优美的现当代小说,如果翻译成了拼音文字,想必也神韵大失。只要读沈从文、老舍、柳青、孙犁、贾平凹等作家所构筑的民族地域色彩浓厚,富有美妙传神东方绘画美特征的作品,相信就会认同了。
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字作品翻译成拼音文字,就必然降低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艺术档次,这又怎么能反映出汉语作家作品的真实水平呢?屈原、李白、苏轼的伟大诗歌作品一经翻译,如果凭译本,他们最多算是三四流的诗人。
相反,一些外国诗人作家的作品,经过中国诗人作家的出色翻译,往往就能凭借汉语言文字诗性美的凸现而提升档次。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普通诗作了。经鲁迅翻译加工,原本自由体作品变为语言工整而且有韵脚、琅琅上口的名篇了。还有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自白派”诗歌,就被诗人岛子和赵琼的翻译加工而声名鹊起。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及其华文、华语的复兴,指望西方只懂得拼音文字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无异是天方夜谭。如果有一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娴熟地阅读汉语言文字的文学作品,那就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勃兴之时。华文的诗人作家努力创造并期待着这一天,而不是期盼西方人设立的某个文学奖项。
(摘自《联合早报》)素材点拨
素材点拨
中国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信仰缺失,因为不知道追求的方向,所以一有相关奖项发布,马上趋之若鹜。诺贝尔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权威,我们应当看淡诺贝尔文学奖,以自信的眼光和态度来欣赏及本土文学优秀作品。
时文选读
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
姜伯静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让很多国人失望了,倒不是因为中国作家没有获奖,毕竟莫言已经得过一次,而是因为我们喜欢的村上春树又一次陪人家读书,又一次成了陪跑者。但仔细想一想,这个结果并不应该让人意外。因为在我看来,村上春树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莫迪亚诺属于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人。与流行元素相比,颁奖思维明显“滞后”于潮流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对于我们来说,莫迪亚诺是一位陌生的“熟人”。与很多“异军突起”的诺奖得主相比,莫迪亚诺在中国的文学市场绝不能算是一个“迟到者”,甚至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作为王小波、王朔曾经顶礼膜拜的“导师”,莫迪亚诺理应被更多国人知晓。只可惜,在王小波早逝、王朔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符号的今天,莫迪亚诺依然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属于另一代人一样。尽管在此之前,他在中国还未属于任何一代人。
但从文学写作本身来看,莫迪亚诺却真的属于另一代人。莫迪亚诺的文字,更多地注重过去、描写过去,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所言,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吴岳添编译的《塞纳河畔》中,有记者问莫迪亚诺当时(1993年5月)正读什么书、喜欢哪一类作家?他回答:“在二十世纪的作家当中,我年轻时印象最深的是从海明威到帕维泽,再近一点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不属于这一代人。”而他从《星形广场》开始的写作,恰恰印证着他的说法。
与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相比,村上春树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村上春树。尽管存在着种种误读,可我们很多人就是宁愿相信村上春树就是“挪威的森林”里的那棵树,就是小资,就是小清新。除去国别、民族的因素,因为喜欢,所以希望,希望村上春树能够得奖。只是很可惜,村上春树属于今天流行的时代,而他的拥趸似乎还没有掌握投票权,他的影响力还很难从民间影响到远在北欧瑞典文学院的那几位老同志,他的作品理念与“创作出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也相去甚远,他的人文理念噱头更是要比“德国占领时期”这几个字差得更多。所以,村上春树还需要再慢慢跑上几年。
其实,很多诺奖得主都是属于另一代人的,包括我们的莫言,因此这并不奇怪。据说,莫迪亚诺某部作品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仓库里还有很多本没有卖出去,借着这股诺奖的东风,不知会不会咸鱼翻身。而我们,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好好阅读一下这个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呢?
(摘自《北京青年报 》2014.10.12)
学生佳作
读书有三重
贾平凹老先生妙用了这样一句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再看水不是水;又看山还是山,又看水还是水……”
山水有三重,读书与品读经典不也如此?
品经典之一重: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格物是致知的前提,品读经典首先要回归到原著,唯有那流传千载,经时间的检验之后仍不露破绽的源头之作才是我们知识源源不断的活泉之水。
读《论语》,你要去吟哦那“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方能体悟大方之家的处世睿智;读《鸿门宴》,你需回归那字字如明玉的方形文字,读句读、品情节,方能获得那兵家之胜败之诀,处世之变通圆滑;读柳永的《雨霖铃》,你得去吟唱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方能感诗人之所感,从缠绵悱恻中体察世间真情。
倘若只从翻译后的书中读经典,文字带着冰冷的面具,何来精髓之悟?
品经典之二重:思之所至,赏玉鉴纹。
愚者如我,读书总是兴之所至,只识文字美不美。思之所至,赏玉鉴纹。真正的经典,字字珠玑,倘若只停留迷恋于文字之美,情节事物之光怪陆离,不免流于浅薄。
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否需要去思考轻与重之间的关系呢?你看看这活过的人生,想想那重虽是一种具体的可言说的负担,可那轻——虚无的轻,未必不比重更沉重百倍。虚无才是人生最难以承受的重量啊!
品经典之三重:自视所存,书已成镜。
王成玉曾言:“从来没有人在读书,而是在书中读自己。去发现自己,寻找自己。”当你在书中会晤先哲与智者,在电火石光中思想激撞的瞬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便是对经典的体察与感悟。
感悟常常流露于生活,生活的体验是对经典的再现。读赵明诚与李清照婚后琴瑟合鸣的时光:他们饭后坐归来堂烹茶,互问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胜者可先饮茶,“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他们把经典之爱延续到生活之爱,这才是经典的再创造再体验。
山水有三重,读书亦有三重。
先格物,再思考,而后看到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人生的绮丽。
午后,如果阳光澄清,往日已归去哪里?在生之极处,在思之极处。在温暖的午后,品读经典,岁月静好。
点评
作者从“格物——思考——看自己”三个层面展开,层层深入,阐述自己对阅读经典原著方法的独到见解。文章处处扣紧“如何阅读经典”这一话题,分析简洁、透彻而又有深度。行文中诗词佳句信手拈来,足见作者丰厚的知识积累,语言洗练,行文流畅,结构紧凑。作为考场作文,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实属难得。